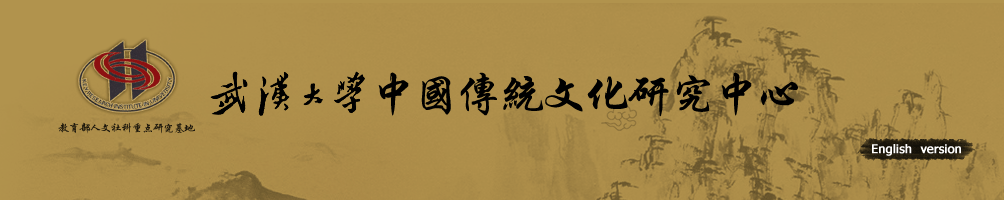“五四”在山东农村
1919年5月中旬,在济南读书的学生回到了诸城县的家乡。他们都是县立高等小学毕业的,那时候的小学是七年制,高小是三年。他们在当地有不少同学,多数都熟识。他们不到6月30日学期终了就放假回家,带来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了抗议巴黎和会瓜分中国罢课的消息;也带来了济南各校学生响应北大学生罢课宣传的任务。他们讲说,欧洲大战协约国胜利了,在法国都城巴黎召开和约会议。中国也是参战胜利的国家,不但没有分享一点胜利的果实,在和会上列强要瓜分中国。日本提出了山东省由日本控制的二十一条款。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是亲日派,在日本代表的威胁下将要签字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为此举行罢课抗议、游行示威,要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他们还讲了,中国当权的北洋军阀压制学生爱国,包围了北大第三院,学生的饮食断绝,激起了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并包围外交官的住宅的情况。这些讲话激起了在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各班都开始议论了。
学校里有两份报纸,一份是上海的《申报》,一份是北京的《晨报》,都在校长办公室里。《晨报》上已经发表了北大学生罢课的消息,校长和教员都知道。可是学生平时不看报,教员又“莫谈国事”,所以学生们闷在鼓里。这时向校长室找报看了。学校当局还有点爱国思想,对学生们的行动明地里不干涉,暗中还支持。
一、反日大会
诸城县城里的高等小学只此一家;还有高小隔邻的两级女学,高级学生只有几十个人,都是城里的大家闺秀。她们出入学校,走上大街,还是低头看脚尖,目不旁视;还有一处单级师范养成所,学员有四五十人,年龄较大,有的是读过“五经”、“四书”的老先生,经过学习一年回去当小学教师糊口。这两校的学生也知道北京和济南的学生罢课游行,却引不起他们的行动,从京、济回来的学生也不大注意他们。他们注意的是高等小学。经过他们讲演宣传,高小学生动起来了,每个班都集会酝酿罢课游行,筹备反日大会。
高小学生有五个班,共有200 余人。首先发动起来的是三年级和二年级,接着人数最多的一年级也跟上来了。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反日会成立选举了三年级的陈宝琨为反日会会长,徐宝梯(我的学名)为副会长。各班排练队伍,剪贴小旗——内容是“还我河山”、“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出卖山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实什么是帝国主义,我们也还不懂。问历史教员,他解释说:“帝国主义就是强国侵略弱国的主义。”县立高小动起来以后又去联合两级女学和单级师范养成所。定于6月7日在西关人烟稠密,商业繁荣的地区开反日大会。两级女学和单级师范能参加的不过几十个人,高小学生200 多人全部参加。一律是灰色的制服、军帽,浩浩荡荡从学校出来,沿途高呼口号。游行路线,本来是出西南小门去西关会场最近,为了影响全城,从南门里出来走南北大街,经过县府前面,出西北门再转向西关。体育教员和历史教员都跟在队伍旁边,指挥员是反日大会推举的。在西关财神庙街高地上搭起一座主席台,台上交叉挂着五色国旗。
反日大会主席是陈宝琨,宣布开会以后,是唱爱国歌。我还记得第一段歌词是:
一统旧江山。亚细亚文明古国四千年。最可怜犹太印度与波兰!亡国史,读之心寒!
共唱了三段歌词,音调怨哀沉痛,无论是唱的人和听的人都感觉心情沉重。下边是讲演,高小学生三个年级都推出能讲演的代表,轮流土台,讲的都是“中国要亡了,同胞们……越讲情绪越激动,讲得痛哭流涕。当他们讲到青岛和胶济铁路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矿山也要归日本人开采,3800万同胞将要作亡国奴的时候,开会的群众,连周围参观的商人想到山东人民的命运,想到自己的命运,齐声痛哭了。三年级的同学王伯年,跳上台去,撕下自己白小褂子的一块衣襟,咬破指头写出了“宁死不当亡国奴”七个字。血书激起的怨愤情绪达到了沸点,由号啕大哭,变成了低头啜泣;呼口号也凄惨嘶哑了。大会宣布游行,把血书挑在国旗上边,举在游行队伍前头。游行的队伍扩大了,没有参加游行的青年们在后边也跟上了。路经商店门口,有的学生停下来向商人宣传,商人们也感动了,纷纷地上门板。一家上门各家响应,一时间上门板拍、拍的声音响彻大街,形成了罢市。
诸城县城离青岛不过130华里,县境离青岛更近,他们知道日本人在青岛欺侮中国人的事实。诸城闯关东的人也多,他们看见过朝鲜亡国,作日本人牛马的惨状。群众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同情的。
二、查烧日货
反日大会以后开始抵制日货,要群众不买日货,不用日货,给日本经济造成损失。红货店——布匹等,挂货店——带子之类,差不多全是日货。火柴是青岛工厂制造的,红白糖是从台湾运来的。如果没收了这些货物,商店连资本都亏损了,也会影响到店员的生活。反日会和商会谈判的结果是,贴上反日会查过的符号,可以继续出卖,卖完了不再贩卖日货。
商界也成立了反日会,商会会长成了反日会的会长。学生查日货,商会来配合。商店老板对于学生是有戒心的,对于商会来的人使眼色、对袖口作出了种种姿态。我们抓不住人家的毛病,明知其中有问题,也提不出来。
中药铺、酱菜园和茶庄是没有日货的,对学生查日表示欢迎,老板在店门外看到学生来往柜台里边让,可是我们也不进去。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茶庄找当二掌柜的舅舅,想了解一些商界的情况。他说:“商会长和店掌柜是一家人,你们几个学生管什么用呀!人家有利可赚,该买进的买进,该卖出的卖出,管他什么国货日货。”我听了他这话,心情很沮丧,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又问:“你们查过瑞华春号没有?”我说:“查过,没有日货。”他哼了一声说:“他们没有,西关就没有日货了。你们真是小孩子。”“你们知道瑞华春东家是谁?”他这一提我明白了。瑞华春的东家是高等小学的于老师。我们平日到西关买东西,常常碰到于老师从瑞华春出来。瑞华春的小楼上是于老师吸鸦片、打麻将的地方。高小的校长和于老师是拜八兄弟,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于老师两个儿子,一个在三年级,一个在二年级。我们的一切活动,他们都知道。瑞华春的日货都藏起来了。我在回校的路上,回想舅舅的这些话,认识到瑞华春的事和于老师及两位同学有关系。那两位于同学和我们在一起,大喊大叫地抵制日货呢?
有一天校长叫了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室内坐着两位客人;都是绸子大褂,黑纱马褂,这是城里绅士们通常的打扮。我以前在学校里也看见过他们,他们和校长是常来常往的客人。今天,当着他们,校长叫了我来干什么?我愣愣地进了屋子,按通常的规矩站在一边,听候吩咐。校长指着一个矮个的胖子说:“这是你的伯父,他愿意认识你这个同姓侄子。”又指点另一个黑瘦的家伙对我说:“按行辈算,你应该叫他表叔,我知道你们是亲戚。”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低下了头,什么表示也没有。他们认为我这个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怕见生人。他们开口赞扬我说:“你们校长和国文老师都说你的作文好,是个有出息的学生。”接着又说:“爱国不仅你们几个学生,现在满城绅商都爱国,参加反日会、查日货,咱们一起干!”我还是不言不语,现出了为难的样子。校长放口要我回去,我转身就走。那二位绅士,屁股离了椅子有半寸算是送我。我出了校长室还听到他们议论我是个老实孩子。
不久诸城各界反日会成立了,学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绅士和老板掌握了反日会的大权,出了很多主意。有一项主意是不让日货进城。从县城到青岛必经之路是离城30里的辛兴镇。在这个镇上安置上查日货的卡子。有一些肩挑贸易的小贩到这里就被查住了,把他们的日货扣留下,拿出一部分来,当众烧毁。逢辛兴集的这一天烧日货让四乡来赶集的人看看。赶集的人把烧日货的场所围起来,点上火以后,货物着了火,烈焰冲天,发出刺鼻的臭味。这些烧日货的人,不是学生,也不是商人,不知哪里来的一些少年人,他们对劳动人民用血汗生产出来的货物烧毁毫不动心。那些小贩眼看着自己的血本丢进火堆想向前抢出一些,被烧日货的人,推出场外。
我们碰上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办才好?总是内心里不安,又阻止不住,心情十分沉重。学校要提前考季考,学生反对,学校干脆宣布不考了——放假。乡下学生纷纷回家,只剩下我们反日会的几个主持人。城里的学生还来办事,那位于同学也在内,非常活跃,他们和本城的绅士、老板很合手。每天下铺子吃吃喝喝。我们几个人呆不下去了,也就收拾行李回家。相约在乡下组织反日活动。
三、在农村查日货
我们村就有几个肩挑贸易的小贩。他们收购乡下的鸡和鸡蛋挑到青岛市去卖了,买上火柴、红白糖、香烟和各色的线等物回来。这些人都是我的邻居和同姓叔伯或者哥哥。我在城里查日货他们是知道的,往常回家到他们那里去,总是很亲切热情地,笑脸相迎;长辈有长辈的样子,同辈有同辈的样子。这次回来不同了,他们总是避着我,我们之间有了隔阂。我就去他们家里,他们见了我很恭敬,不像从前那样自然。他们的精神,显示出很不安。我环顾他们的小破屋,他们更为难了。自动地说:“穷,没有办法,做点小买卖,又碰上这年头,你说怎么过呵?”他们的话是实话,我没法说不对。正在这时候买火柴的人来了。“大叔:我买封洋火。”这位大叔回答说:“卖完啦。没有啦。”买火柴的在门外叫:“刚才还有人来买过,怎么一回就没了呢?”说着进了屋子,看见我在这里也就不再问有没有了。以小贩为生的人没有土地,不作小贩就不能生活;火柴是一天也离不开的火种,没有火柴就要回到火镰火石的时代去;而且打火工具早已没了,今天一时也弄不来呀。我看到这情形,不能不说话了,我说:“查日货,本来是为了爱国给日本造成经济困难,不是和自己的同胞为难。有就卖给他一封吧,卖完了不办日本货就是了。”卖者听了这话果然拿出一封来。也许是买火柴的出去透露了风声,买火柴的连三接四地来了,他们害怕买晚了买不到,以后没有火柴用。
我又问:“大叔没有别的生活吗?”他回答说:“没有土地,还能做什么?打短工,挣个肚里饱,家里这两口人吃什么?”说着话,眼圈里含着泪水。这位穷大叔因为欠账借了高利贷,还不起把两亩薄地卖了。自己跑到关东去,老婆带着一个孩子要饭吃。闯了几年,回来时还是双肩托一口,没有剩下什么。在关东男人多,女人少,闯关东的多是男的,不能成家,怎能传宗接代,还得回来找自己的亲人。回来以后借了同姓近友的一个地角,盖了一间土打墙、草苫顶的屋子。把剩下的两块钱作本跑青岛、做小买卖。一家三口人,吃这条扁担,遇上阴雨风雪天气,不能出去,在家里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这次从青岛回来,为了躲避查日货,放夜站、走小路,才回到家来。
这家同姓邻居离我家最近,我小的时候常到他家听他讲青岛的火车、汽车、大楼马路,像听神话那样有趣。今天能查他的日货断绝他的生路吗?当然不能。正在这时候来了买线的,他不再掩饰拿出一把来劈给顾客一缕。我说:“多买卖这些不行吗?”大叔听见笑了说:“你们天天查日货,您知什么是日货吗?带轱辘的线是日本货,不带轱辘的就不是日本货吗?实说了罢:这些线也是日本工厂出的,把日货查净,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做了,大家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你若一点日货不沾,就得光着身子,烧掉书。”
我从这间破草屋出来,心情十分沉重,这教育太深刻了。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住在青岛附近各县的人民,旧用的火镰火石丢了,专用日本工厂出的火柴;我们把纺车织机丢了专穿日本工厂织的布;就是针头线脑都取给日本。为什么日本人要割去山东,他们早把山东人的生活命运掌握了。我们抵制日货,拿什么样的国货来代替它呢?在城里查日货的时候知道双龙牌的洋布不是日货,那也不是国货,那是英帝国主义进口的布,查日货用英货,这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这些问题在我这个少年心灵里,像波浪似的翻滚。
我也曾听到来往济南和北京升学的同学们讲过,他们都是从高密火车站上车。胶济路日本在欧战期间从德国手里夺过来以后就归他们所管辖。中国人拿着银元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不能买火车票,必须拿银元和中、交两行的票子到车站上的日本商店换成日本正金银行的票子才能买火车票。这些在济南和北京反日爱国的学生,也是这样才坐上火车回到家乡的。他们不能自背行囊,或者雇骡马车走十天半月才回来呀,那样,一月的假期不是光在路上了吗?我是准备升学的,也准备低着头咬紧牙关去作自己不愿作的事情。我觉得小贩大叔值得同情,如同对学生们不得不用日本钞票买火车票一样的同情。今天我查日货断绝小贩大叔的生路,将来自己为了不坐日本火车就不升学了吗?回想起自己也参加了烧日货的行动感觉内疚。
日货不能不查,痛心的事情还要去做,亡国奴的前途摆在面前,出路在哪里?那时发生了狂想,想到和日本人拼命,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挣一个,中国人多,日本人少,最后是中国胜利。
我们村里还有一家小铺,是一家小地主开的,专卖油盐酱醋茶和一些零碎土产货物。他们不是不卖日货是很快就卖完了,看见我们学生就自动招呼我们去查,当然是没有日货以后才有这种表现。可是他们卖的货一律涨价了。本来一个铜板可以买十片火纸,现在买五片,他对顾客态度很蛮横:“不买,过两天一个铜子一片也买不到,嫌贵,贵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这家小铺乘机发了财,洋洋得意。村民只能用白眼珠子瞪他。
四、在农村开反日大会
诸城县城北昌城区是最富庶、最文明的一个区。围绕着昌城镇的村子都有个小学,也有在县立高小读书的学生。联络高小学生和各小学的老师,就可以开成一个反日会。要动员小学参加也要接触各校的董事长。他们是当地的绅士,小学都是他们办的。这些董事长都知道我在县立高小作过反日会的副会长,所以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满口满应地参加反日大会。尤其是隋家官庄有个隋理堂老先生,他是动员我祖父送我人高小的前辈。他在清朝是个秀才,现在是山东省议会的议员。他又是同盟会的会员,见过孙中山先生,竞选过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没有成功。他对我奔走开反日会极口赞成,夸我爱国,答应我一定到会,并且叫出他的大姑娘隋焕东和我认识。
隋大姑娘,不只我这样称呼她,县城甚至省城的一些知道她的人都这样称呼她。她年纪约二十二三岁,山东省立女子师范毕业,现在县立两级女学当教员。细高条身材,四方脸、大眼睛,头上梳了两个蘑菇髻,上身穿爱国布(其实也是英国纱织的)短衫,下身是黑绸裙子。那是袖齐手腕,裙扫脚面。在县城开反日大会的时候,两级女学是她带队。因为在县城组织反日大会是互相知道的。那时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不能随便谈话。她在自己家里见到我,说话很开朗,我倒显得很羞涩。叫她什么呢?不是同学,又不是同事,叫她隋老师又太尊。我叫隋老先生表大爷,顺口叫她表姐,她却按省城男女学生因公接触的习惯叫我徐先生。
反日大会的会场设在刘家河岔,离我家只有二里、十几个村子最远的东老庄也不过五里。这十几个村子,共有十处小学。刘家河岔的张校长得知会场设在他那个村子里,十分欢迎,答应布置会场的一切。
若是按今天的习惯只要打扫出一个会场地址来,挂上国旗,一切都完了。学生可以自带小板凳和小马扎就行了。可是那时上层人士认为和农民一样矮坐不成体统,所以会场要放下小学的凳子,还不够又向村民借了一些,会场里的坐位全是凳子,而且摆得很整齐。会场周围的树上和墙上贴满了标语。
隋老先生指定他们小学一位教师——曾跟他在省城活动的人——作司仪。第一项是推举主席:张校长推举隋老先生,隋老先生推举张校长。最后还是张校长,恭敬不如从命当了主席。
城里的绅士只要是出大门就穿大褂马褂,热天也不穿短衣出门。我们高小学生在乡下没有穿大褂的习惯,弄个大褂进城时就穿上,出城就脱下来,在肘窝里夹着。在城里不穿大褂,如果被校长和老师碰上,就要因为“不敬”记一条过。这天反日大会上,乡下教师一律不穿大褂,只有隋老先生和张校长都穿大褂,不外加马褂,就算是常礼服了。隋大姑娘还是在学校里上课时的打扮,就不能不惹得乡下人注意。特别是乡下妇女看到一个大脚板、长裙子,头上挽着两个疙瘩的姑娘,觉得很是稀罕。
秩序单上第一项是宣布开会,第二项主席致开会词。这位张校长是到过济南的,有人说他到过北京。平日他讲的是本地话,上了主席就讲“官话”了,表明自己不是一般的乡下老,是走了官场,见过世面的。他的话小学生们听不懂,教师们听到有点惊讶,想不到他是个乡宦。
在第三项——讲演,宣布以后隋大姑娘向两边的人略作谦让之后,缓步上了主席台了。教师们带头,小学生们跟着鼓起掌来。这时不仅会场里的目光集中向她,周围的墙头上树杈上都上去了人。他们,也有她们从来没见过大脚板,走起路来一掀一掀的样子,也没见过长裙子、蘑菇髻。会场周围抬着筐、扛着锄的男人也聚了不少。我看到会场里有一部分凳子空着,想去招呼他们来坐下听听,可是我不到他们面前还好,到了他们面前,他们抽身回头就走了。再走向几个也是同样,像是赶他们走似的,我就停止招呼了。
这位大姑娘在济南女子师范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位活动分子。今天在小学生、小学教师面前她毫不拘束。她向场子前一鞠躬就讲话了。第一句就是“同胞们”。她的讲话好像早已背熟了:从日本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先从山东下毒手;全国四万万同胞,山东3800万同胞要当亡国奴开头,越说越激动,忍不住声泪俱下,呜咽的听不清讲的什么了。台下的教员学生被她激情所感动得也纷纷落泪。司仪趁这机会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本货!”台下也跟着呼喊。她在讲完了话下台的时候,还用手绢抹眼泪。
接着各校的教师有两位讲演,都是有准备的背讲词。隋家官庄小学的学生,十三四岁四年级生也上台讲了背熟的词。最后一项是喊口号,经过开会学生们也习惯了,口号喊得有点声势了。
这次反日会开过以后,我们也没有查日货,乡村里依然风平浪静。
五、新旧文艺的斗争
诸城县立高小的校址是清朝时代的观海书院,这是一些秀才进修的地方。全校七名教职员中就有四位是秀才,那三位刚在师范学校毕业的,被社会上和学生瞧不起。国文课本是文言的,有现代编写的,也有选自古人文集的。例如:白居易的《凌霄花》和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国文教员讲完之后要学生背诵,所以至今我还能背过几句。现代编的课文,老师说不用讲,要学生自己阅读,也不要求背诵。课本以外还从《古文观止》里选一些文章讲读。韩愈的《原道》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古文观止》中是篇幅最长的了,我们都能背出来。
作文时谁把八大家的文章套上就得到好分数。秀才教师还拿这些“好”卷子给县城的举人、翰林老爷看,表示“斯文未坠于地”。举人和翰林老爷看了满意之后,高起兴来,在后面批上几句夸奖的话。谁有篇这样的作文,不仅全校欣羡,连本城的好文绅士都知道。
学生们自修常常是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对此学生们并不满足。认为梁启超的文章像流水一样,经不起思索推敲。对梁启超给蔡锷拟的讨袁世凯称帝的文电《盾鼻集》,认为是慷慨淋漓、纵横恣肆,使人快意。还爱读林琴南的《畏庐文集》。林的文章是难懂的,越难懂越爱读,叫人看不懂的才是好文章。学生们也爱读《枕鸦浪墨》和苏曼殊的爱情小说——都是文言体的。
胡适的《尝试集》传到诸城高小以后,引起了学生们议论纷纷,这些从古文堆出来蠹鱼,拿语体文不当作文章看。他们择其中的语句开玩笑。例如,看到两个要好的同学携手同行,就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又如搞一件事情失败了,又引用《尝试集》的句子“尝试成功自古无”。
《新青年》杂志在学校出现以后,由于思想先进,道理讲得透彻,受到部分学生的欢迎,从北京带来的少数几本,常常你传给我我传给他,没有没人看的时刻。
这年冬天学生们从北京弄来了新剧本,组织演新戏,庆祝新年。没有女角,只好男演女。这地区闹春节踏高跷、跑旱船、跑驴都习惯男演女。新剧在学校出现,校长和教师因为北京的学生也演戏,持一种不问不管任其自然的态度。在校内排练一些日子,演两场校内学生自己看,也不到社会上公演,这样还引起校外社会上的不满,批评说:“学生不读书,演戏,和戏子同流,要不得。”校长是自称有革命思想的,但逢迎社会上“舆论”又说:“逢场作戏,偶尔为之,未尝不可,不要因此荒废学业。”
1920年春季,学生作文也出现了白话的卷子,而且是受过举人、翰林品题的学生。文章讲道理条条有理,读给别人听明明白白。于是国文教员老秀才又得出一条结论,说:“文言写得好的,白话文才能写得好。你们看写白话文的××同学不是咱班里文言写得最好的吗?”在教员的挑拨下,学生还是写文言文。可是任凭秀才们怎样阻挡,《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等书在学校里暗中流行,上班时在桌子底下看,上学习课的时候上边盖上课本偷看,有时被查堂的教师揪出来。熄灯以后在被窝里点着香头看。老师没收了学生的书以后,自己在屋里也看迷了,学生闯过去要书,只好还给他们。
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实习编辑:念念)